我与篆刻(图)——王来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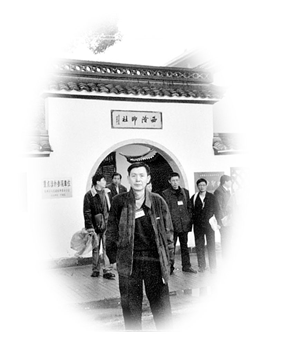
作者在杭州西泠印社留影
我学习篆刻是付出了代价的。由于常年伏案,40多岁便驼了背,执刀,握石,又使左手大拇指韧带受损,不能弯曲,医生告知,没救了。这一切,怨不得别人,都是爱之心切所致。
我的父母不识字,没有艺术基因传承给我,但我却鬼使神差地喜欢上书法、篆刻这种文化人干的事情。小的时候,记得父亲有两方石头印 章,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篆刻实物。印章没有刻边款,不知出自谁人之手,石材像玉石一样,光润细腻,方寸天地中那富有美感的线条变化和古朴典雅的艺术风格,引起我的极大兴趣,从而产生动刀尝试的念头。从少年时代至今,40余春秋里挥毫、耕石,乐此不疲。小时候,既无师承,又无书籍,一切由着想像发挥。按行家的话讲,这叫不得法,难上道。“文革”末期,我有幸认识了林鹏、水既生、邓明阁等省内书法篆刻名家,从此,循着他们指点的路子,一步一步往前挪。
当时,最头疼的问题是刻印的石料市面上难以买到,主要用磨平的砖头和自制的石膏片来代替,效果欠佳。后来听人说,离家10多里外的一个玻璃制品厂有这种石料。我兴奋至极,找了一个小麻袋,骑着自行车就奔向那里。与传达室的老师傅说了许多好话,方允许我进去拣几块石头。时逢数九天,西北风呼啸着,路上的冰块儿能照见人影,不小心,连人带车摔到地上,六七十斤重的石头压在腿上,又冷又疼,好在处于兴奋状态,疼痛不是事。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拐着腿推着车子回到家的,晚上,连夜开工锯石,响声扰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。
刻印的前提是必须懂古文字学,善书法。此时,“文革”已结束,艺术的春天开始复苏,书店的货架上渐渐有了这方面的研究资料,文化用品商店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,也摆上了宣纸、石料。只是囊中羞涩,买书、买材料还得从孩子的奶、糖费用中挤兑。
1985年,省金石书道研究所为了发展壮大太原地区的篆刻队伍,所长李元茂先生邀我担任授课老师,让我心中很是不安,生怕误人子弟。记得光明日报的梁衡先生、山大艺术系的李德仁教授以及崔耀南老先生等都给了我一定的鼓励,使我在教授别人的同时不断地提高、充实自己。
1990年,省天龙印社成立,省书协主席徐文达、林鹏等前辈又推荐我担任印社副社长。同年,我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。前辈的教诲、鼓励、扶植使我深受感动,也更加激励我沿着这条艺术之路不断探索、前进。
2003年秋末,我赴杭州参加西泠印社百年华诞,在孤山脚下临时搭建的露天会场上,人头攒动,座无虚席,此时天空忽然降下绵绵细雨。包括来自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二千多老少篆刻家,无一喧哗和退出会场,人人都珍惜这一生一遇的百年盛会。此时,我被深深地震撼:中国的传统印学文化竟有如此大的魅力!
我热爱书法、篆刻艺术,几十年来我与它们寸步不离,它们已成为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把对家人的许多爱分割给了它们,我爱它们,是因为它们倾注了我太多的精力和情感;我感恩它们,是它们引导着我一步步走向文学、艺术的殿堂,去荡涤心灵的污垢。对我而言,假如没有书法、篆刻,我的精神世界将是空虚和平庸的。
人生的选择各有不同,我选择了书法、篆刻。虽然这条道路很艰辛,我还是要一如既往地走下去。
一九八三年山西省金石书道研究所第一届篆刻班结业留念
右二为海南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李元茂先生,右三为老书法家崔耀南先
生,右五为王来和,右六为沈晓英女士。




